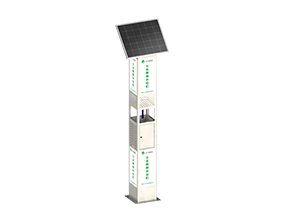錯誤。只要說一句話,人們就會感到害怕。“To bug”是煩擾、惹惱的隱喻。當有人“出錯”時,他可能是在慌亂,也可能在趕緊逃離現場。也許你得了嚴重的“腸胃病毒”。飛翔、爬行、爬行、匆忙爬行、爬行、懸掛、蕩蕩、游泳的蟲子。人們為什么愿意一輩子與這些生物保持密切接觸?
事實證明,蟲子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陌生。當然,它們可能有六條腿(甚至更多),但就像我們稱之為家的這顆藍色大理石上的萬物一樣,昆蟲是我們生態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在進入細節之前,先把一件事弄清楚,就像黃夾克的毒針一樣:當我們提到“蟲子”這個詞時,到底指的是什么?要回答這個問題,我們需要談談分類學,也就是生物的命名和分類。
基本上,“蟲子”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動物之一,隨意地說:蛛形綱和昆蟲。蛛形綱動物有四對腿,身體分為兩節——比如蜘蛛、蝎子、螨蟲或蜱蟲。而昆蟲則有三對腿,身體分為三個節段(頭部、胸部和腹部)。也許再加上一對翅膀,你就能得到一只完整的昆蟲。
昆蟲和蛛形綱都屬于節肢動物門,該門還包括一些我們稱之為昆蟲的其他動物,如蜈蚣、龍蝦和螃蟹。在本文中,“蟲子”大致指所有節肢動物,但我們主要討論的是昆蟲。既然我們已經知道自己在研究什么,就需要進入重點:為什么?
除了偶爾在家里看到蜘蛛或蟑螂外,你大概不會太多去想蟲子。然而,它們在我們的生態系統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——無論好壞——我們對它們的了解越深,我們的生活就越有利。
內容
詭異的后果
與蟲子共處的起伏
蟲子很酷
詭異的后果

有些昆蟲是有幫助的。例如,你可能知道蜜蜂數量正在減少,這對我們的食物鏈有嚴重影響。昆蟲學家希望了解這一下降的原因和后果,因為這項免費授粉服務與我們的農業經濟有著直接聯系——金額達15億美元[來源:霍爾德倫]。蜜蜂和其他昆蟲負責為我們依賴的許多作物授粉,就像大多數堅果和水果一樣。
另一方面,許多昆蟲則導致農作物的破壞。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昆蟲啃食植物的果實、根系或身體造成的損害。例如,黃瓜甲蟲的食欲是不分彼此的。成蟲黃瓜甲蟲會吃它們喜歡植物的果實、葉子、嫩芽和花朵,而它們的幼蟲則喜歡啃食黃瓜的根。蚜蟲等昆蟲還可能將病毒、感染和疾病帶入農作物,造成廣泛的破壞。
更復雜的是,20世紀初我們開發了化學農藥以減輕問題昆蟲的破壞。但真正的問題是自我造成的:在消滅有害昆蟲的同時,我們也消滅了有益的昆蟲——就像化療殺死癌細胞,但也會消滅健康細胞和組織一樣。如果昆蟲學家能學會有效針對有害害蟲,有益昆蟲有望恢復生態系統的平衡。
昆蟲不僅僅是野外的問題。它們也會入侵儲存的食物,在溫馨的小麥倉里吃東西和/或筑巢,或者在你儲藏室后面那盒被遺忘的Bisquik里。當然,蟲子的興趣并不限于素食者。有些吹蠅物種的當初幾周生活在宿主的肉體中,以周圍的肉為生。跳蚤和蜱蟲可能導致貧血,而角蠅則以牛為目標,每天可消耗多達一品脫的血液。昆蟲學家幫助我們理解昆蟲的生命周期和行為,從而幫助我們保護自身的食物供應,預防食源性疾病。
與蟲子共處的起伏
蟲子可能會吃掉并傷害我們的食物,但我們可以反擊——通過吃掉它們。也許你見過旅游頻道主持人安德魯·齊默恩飛往臺北或厄瓜多爾,吃一些繭和蠕蟲,無論是熟的還是生的蠕動。對于膽小的西方觀眾來說,這簡直令人作嘔。但從經濟(和歷史)角度來看,這很合理:昆蟲無疑是豐富且營養豐富的蛋白質來源,然而幾乎整個西方文明尚未普及。昆蟲不是解決全球糧食短缺的萬能辦法,但它們是有效的補充劑。
雖然我們與昆蟲和食物的關系一直顯而易見,但我們與昆蟲和疾病的關系卻不然。瘧疾在人類身上已有數百甚至數千年的歷史,但直到1880年,一位名叫查爾斯·路易·阿方斯·拉韋蘭的法國軍醫才在一名瘧疾患者血液中發現寄生蟲。十七年后,即1897年,一位名叫羅納德·羅斯的英國軍官成功證明蚊子傳播瘧疾寄生蟲。有了確鑿證據表明昆蟲能攜帶疾病,對昆蟲的迷戀不再是愛好;這是我們生存所必需的科學。
或者來個更性感的例子?你聽說過接吻蟲,也就是刺客蟲嗎?雖然所謂的“接吻病毒”有數十種,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本地種類可能攜帶查加斯病,每年導致50萬人死亡,總共感染約000萬人[資料來源: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,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]。查加斯病的傳播實際上是“死亡之吻”:致命的寄生蟲寄生在親吻蟲的消化系統中,進食后被蟲子排出,通常在夜間靠近受害者的嘴巴。無意中的受害者可能會昏昏欲睡地擦拭或抓撓咬痕,將寄生蟲引入血液中。如果不及時診斷,寄生蟲可能會引起輕微、非特異性癥狀,如嘔吐或腹瀉,最終引發更嚴重的并發癥,如心臟擴大或心臟驟停。僅就親吻蟲和查加斯病的地獄科幻故事而言,蟲子絕對值得研究。
諾貝爾·施莫貝爾
有趣的是,羅納德·羅斯因發現蚊子傳播瘧疾寄生蟲而于1902年獲得諾貝爾獎——早于當初發現瘧疾是寄生蟲的人。查爾斯·路易·阿方斯·拉韋蘭因其工作于1907年獲得諾貝爾獎[來源:CDC]。
蟲子很酷

說實話——蟲子就是酷。我們為什么不想研究它們呢?
以白蟻群體的社會結構為例。白蟻群體按種姓組織,每個種姓都有其功能。你遇到的任何白蟻都是生殖、士兵或工蟻階層的成員。無論白蟻是雄性還是雌性,無論是士兵還是工蟻,它都是無菌的。只有生殖階層的成員才能做到這一點:繁衍后代。如果某個種姓人口過剩,白蟻會通過食人來恢復平衡。
但僅僅因為某件事酷而學習,往往不會吸引到科研資助。我們作為人類可以從自然科學中學到的重要教訓是謙遜。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,在昆蟲領域很可能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。
想象一下在混凝土上鉆孔:你身體前傾,試圖用力對抗堅硬且不受歡迎的質量。這很難。那么,一只像羽毛一樣輕盈的角尾蜂,怎么能如此輕易地鉆進樹木呢?為了弄清楚,昆蟲學家們仔細觀察了那條“角尾”。尾部實際上是兩根針,通過“相互推開和加固,像拉鏈一樣”緩緩進入木頭“[來源:Goldenberg和Vance]。事實證明,這種設計理論上可以幫助宇航員鉆入火星甚至小行星表面——在那里,利用體重無法有效,因為幾乎沒有重力。當昆蟲學家研究昆蟲世界時,他們可能會解決我們甚至不知道存在的問題。
盡管有些昆蟲相當可怕,但絕大多數昆蟲和蜘蛛對人類是有益的——或者至少,它們是無害的。據史密森學會稱,“在任何時刻,大約有10萬億(10,000,000,000,000,000)個體昆蟲存在。”新的估計顯示,地球上每人對應超過000億只昆蟲。雖然這個數據可能會立刻讓人聯想到恐怖電影里蛆蟲和成群的蚊子,但請放心:蝴蝶也是蟲子,滾滾的蚊子和那些友好的小瓢蟲也是。
重要的是,請放心,你比地球上比較大的蟲子大好幾倍。新西蘭的巨型螽蟲體長可達3英寸(7.62厘米),體重可達1.5盎司(42.5克)。雖然對蟲子來說算大,但比普通鞋子或卷起來的報紙小得多。昆蟲學家會確認,螽蟲不會(也不會)把你的孩子帶到中土世界,也不會把你活活吃掉。至少,可能不會。
作者的話:我們為什么要研究蟲子?
作為佐治亞大學的文科本科生,我被要求修兩門科學課程:一門是“物理”學科,另一門是“生物”學科。大一學期我很興奮地選了地質學課程,但我真的很害怕完成那門生物科學課程。我不確定當初是什么促使我選修昆蟲學導論,但從頭一天開始的每一節課都令人著迷。我依然是個終身的業余“蟲子”愛好者,除非其中一只蟲子爬到我身上。